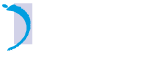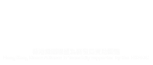【舞蹈新鮮人2022 | 新時代的真摯反思】
文︰胡筱雯
要形容三位「舞蹈新鮮人」的作品,筆者會聯想到情感焦慮、美學焦慮和存在焦慮。彭春的《關我咩事?》從泛濫的資訊談到舞蹈如何表現情感,劉燕珺的《Observing incorrect correctness》思考舞蹈中「美」的定義,董仲勤的《數位世界絕對的0與1》則叩問如何度過毫無目的的時間。這些作品,都啟發自三位新晉編舞對生活體驗的真摯反思。
彭春、劉燕珺和董仲勤,這三位「舞蹈新鮮人」的來頭非常不同。彭春的舞蹈風格以流行編舞及街舞為主,曾為藝人伴舞及編舞;劉燕珺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,主修芭蕾舞系,既是編舞也是舞蹈老師;董仲勤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表演系,參與不少舞蹈及戲劇演出。年輕的他們袍袱不拘泥於舞蹈的形式,而著重舞蹈如何表達自我。
攝:Worldwide Dancer Project(照片由香港舞蹈聯盟提供)
彭春分享,最初他是一邊哭泣,一邊寫計劃書的,讓他想到創作與情緒有關的作品,以舞蹈尋找自己內在未被世界「磨鈍」的感覺。他的作品名為《關我咩事?》,自然讓人想到現今世界資訊發達,在地球另一邊的人的消息,幾秒後就傳到我們耳中,但我們面對這些資訊時,總覺得資訊與自己有關又無關,讓彭春反思自己與自我的關係,「我是否了解我自己?我是否與自己相關?」所以面對自我的情緒,是這個作品的核心。
攝:Worldwide Dancer Project(照片由香港舞蹈聯盟提供)
攝:Worldwide Dancer Project(照片由香港舞蹈聯盟提供)
至於劉燕珺的作品《Observing incorrect correctness》,也啟發自她的個人經歷。劉燕珺是芭蕾舞舞蹈老師,她教的學生由十幾歲到六十幾歲,不同程度的人皆有,而她發現因為自己的舞蹈訓練,教學過程很快會判斷到什麼動作是正確還是錯誤的,然後會說學生的動作「核突」,於是她反思什麼是身體的美和不美?她把創作重心置放在「當代芭蕾(contemporary ballet)」的脈絡下,把觀眾帶到博物館現場,想像舞者以展品的姿態呈現在觀景面前。
攝:Worldwide Dancer Project(照片由香港舞蹈聯盟提供)
攝:Worldwide Dancer Project(照片由香港舞蹈聯盟提供)
最後一位編舞董仲勤,他的舞蹈表演以著名荒誕劇《等待果陀》為創作原點,強調思考與跳舞的關係,應該思考再跳舞?還是跳舞後再思考?劇中角色維拉迪米爾與艾斯特崗正正有過相關的討論。荒誕劇起源於虛無主義,而在現今數據化的世界,人類越來越像是函數機中的一個數據,有什麼存在意義呢?《數位世界絕對的0與1》這作品,想探討「漫無目的的人,在一個發展過度的世界,我們如何用我們的時間」。
攝:Worldwide Dancer Project(照片由香港舞蹈聯盟提供)
攝:Worldwide Dancer Project(照片由香港舞蹈聯盟提供)
對於彭春而言,舞蹈是「有口難言」,身體或許比語言更能表達情緒,希望觀眾在作品中看到自己;劉燕珺將會穿上足尖鞋,在舞台上與舞者演出一個參觀展覽的過程,突破觀眾對芭蕾舞的期待與想像;而董仲勤將會為觀眾帶來「遊戲性」的舞蹈,希望觀眾反思「如果沒有希望,是否仍然願意繼續等待呢?」舞者將以身體語言呈現希望與失望的交替更迭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節目資料
「舞蹈新鮮人」系列 2022:彭春、劉燕珺、董仲勤
9.12.2022(五)|8pm
10.12.2022(六)|3pm
10.12.2022(六)|8pm*
11.12.2022(日)|3pm
地點 :葵青劇院黑盒劇場
票價 :$200
*設有演後藝人談
詳情 : https://www.hkdanceall.org/?a=doc&id=953
==
胡筱雯
獨立藝文記者,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生,主修編劇